作者:﹝英国﹞伊恩·费格逊(Iain Ferguson)、罗娜・伍德沃德(Rona Woodward)作者简介:伊恩·费格逊(Iain Ferguson)是英国西苏格兰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Scotland)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学荣誉教授,除了《激进社会工作实务》外,著作与合著有《反思福利:批判的视角》(Rethinking Welfare, 2002)、《夺回社会工作:挑战新自由主义与促进社会公义》(Reclaiming Social Work: Challenging Neo-liberalism and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 2008, 有中译本)《心灵的政治:马克思主义与精神痛苦》(Politics of the Mind: Marxism and Mental Distress, 2017。繁体中译本改名为《精神疾病制造商:资本社会如何剥夺你的快乐?》)等。
罗娜・伍德沃德(Rona Woodward, 1964-2014)于1990年获得社会工作者资格,并在伦敦和苏格兰东部地方社会工作局服务工作了10年,特别关注处于危险或有需要的儿童和年轻人,包括年轻罪犯。他于1999年获得刑事司法硕士学位,在爱丁堡大学担任犯罪学研究员,并在格拉斯哥卡利多尼亚大学(Glasgow Caledonian University)和后来的斯特灵大学(Stirling University)教授社会工作。
注:原载《激进社会工作实务》(Radical social work in practice, 2009)72-78页。 “主流社会工作者”原文为“state social work”,指在主要接受政府资助的机构工作的社会工作者
翻译:杰克
校对:皮皮瓜、告也
编辑:若愚

在焦点小组的讨论中,一些社工常常强调他们在主流机构中不得不承受的压力和限制。一些局外人看待主流社会工作,会认为社工的压力主要与这些有关:他们不得不处理的困难、不情愿的工作以及有时候咄咄逼人的服务使用者。同样,他们相信焦虑跟他们不得不作出艰难的决定有关。例如说:是否要把受虐待或疏于照顾的孩子与其父母分开;是否在有严重或持续的犯罪时建议进行社区处置(community disposal);或者是否支持患有精神健康疾病的人强制入院。然而,不管是前文提到的Jenny第一份工作和焦点小组成员们的经历,都是社工被要求去给无情的政策收烂摊子,相较于与服务使用者和照顾者工作时提出的挑战,组织和管理的变化对社工的福祉更加有害。
这一章将会展开讨论,在主流机构进行更具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实践何以可能。
我们要重申,社工说过的话,会被用作说明社工从业者每天在多大程度上把服务使用者和照顾者的需要和权利放在工作的中心,而不是苟且度日的程度。这不是说主流社会工作者对他们工作的复杂性有误会,而是说,虽然大部分进入这个专业的人是想帮助他人,但他们同样认识到帮助一些人可能意味着对另一些人行为的控制。用Craig的话来说:
“刑事司法有一些约束,是一种基于法院命令的关系,它不是一种平等的…所以你不能假装完全配合工作…但工作关系依旧是刑事司法的核心…你得先建立的关系,找到这个人问题的核心是什么,然后尝试制定共同的策略去处理那些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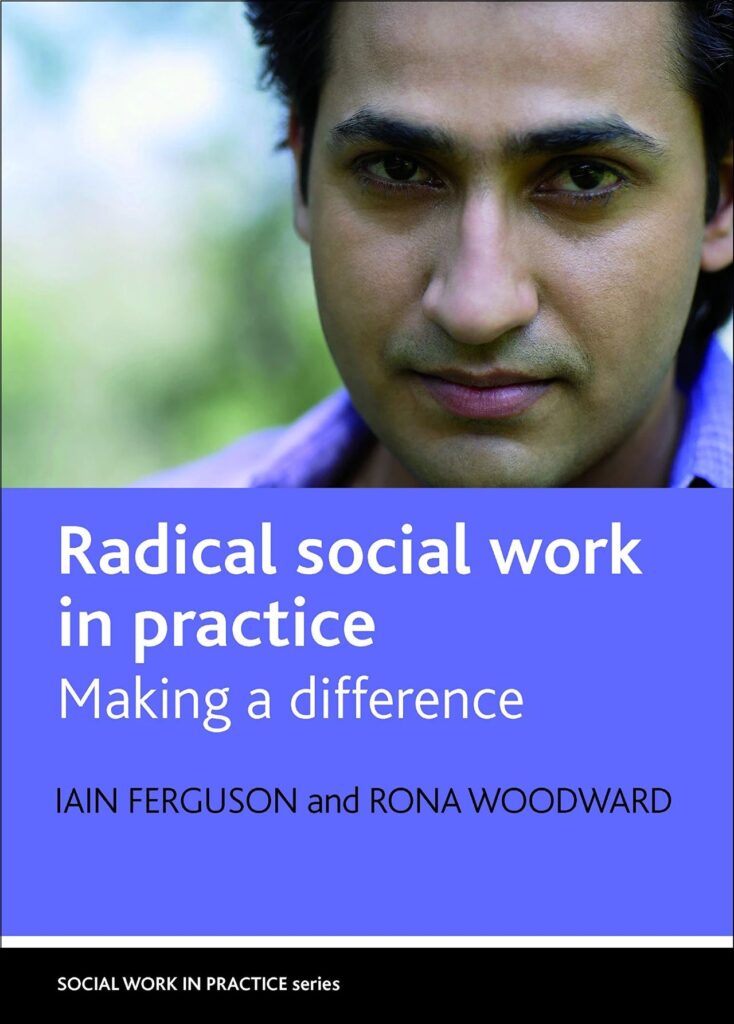
如前所述,焦点小组由坚定顽强的社工组成,所有人都看到了另类社会工作实践的可能性。随后的评论回应了‘21世纪前几十年的激进(或者一种更具抵抗性的)社会工作看起来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社工谈到的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的普遍承诺(broad commitment),认识结构性压迫的影响以及寻找团结志同道合的同工一起捍卫社会工作的价值。
对Conor来说,1970年代和现在的激进实践,都跟综融取向和社区导向(generic and community oriented )的实践有关,他和他的团队努力坚持这种做法:
“很重要,很重要的是我们不是碎片的和过度专业化的…我们走到所有社区和人群中去的能力是极其有价值的,小小的激进实践也是有价值的,因为现在没有人在做了…我们应该找回那种方式。”
Conor意识到他工作的农村环境本身也许就是适合综融取向的,适合满足本地需要的社区导向。然而,对Craig来说,刑事司法服务的专业特性则是要不断改善对犯罪者的服务,因为:
“我作为一个普通社工(generic worker),过去其实是儿童和家庭的社工…儿童的服务的需求优先于一切…当时没有刑事司法服务…专业化当然对情况有所改善。”
尽管如此,Craig认识到,专业化队伍之间实际上互斥的程度有多大:
“上面的人没有认识到:我们真的需要一起手牵手合作。有时候感觉专业队伍之间实际上在互相对抗。”
通常,高层管理者会受到焦点小组成员的严厉批评,但Frances举了一个在高层可以做得更有创造性的例子:
“一个在社区参与了高调犯罪的服务使用者会引起许多的不安…但在那背后是一个非常受伤的年轻人…在一个儿童听证会上…由于社区里的强烈反应,当时这个年轻人正被妖魔化,并被边缘化…《反社会行为条例》…是可以要求地方政府将他赶出出社区的。幸运的是,地方政府强有力地挑战了条例…支援这个年轻人和社工,为这个年轻人据理力争,使其继续留在社区。看到管理者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支持这个年轻人,而不是下意识(a knee-jerk reaction)说“让他滚出去!”,这跟社会工作是契合的,很棒。”
类似的,Kathryn自己团队的管理者全力支持在成人服务里尝试为受压迫的服务使用者的权利发声:
“我们的团队秉持着强烈的社会工作价值观…我们不畏惧挑战体制,我们有很好的领导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像一股力量…在坚持创造这样的对话。”
回到Conor之前倡导的社区为本的理念,Robert也看到了他们强有力的论据,但他觉得他所在的大城市的地方政府暂时忽视了这一点。相反,他认为复兴技能实践在当下的环境给激进实践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
“你知道的,我们认为做一个在行的社工实际上就挺激进的了,这个想法得到了认可。”
对Amy来说,任何实践上的激进主义都要在自己的实践中把个人责任放进去,这样可以保证她能同时照顾好自己,也保持对服务使用者需求的关注:
“如果我们不将一些个人责任带到实践中去,我们只会变得更加区隔,更加压抑,更加妖魔化。对我来说那才是激进实践,它让我时刻保持敏感,不允许自己妖魔化。”
对焦点小组的一些成员来说,实践中的激进理念在他们与服务使用者的工作中得到最好的说明,通过他们与服务使用者建立的关系,他们对服务使用者需求和权利的的关注,他们个人对服务使用者所面对的压迫和歧视的认知。尽管,对其他人而言,激进主义更多是关于用不同的方法将不同的个人和群体联合起来。
对Conor来说,是需要跟在地社区的成员直接一起工作:
“我们应该和在地社区以及其它机构的人一起去挑战压迫,挑战我们被政治家操控的生活方式。”
类似的,对Kathryn来说,激进主义是让服务使用者和团队成员共同参与:
“改变与你互动的系统…如果你把自己看作是机器中的一个齿轮,那你就没有任何力量了。”

第六、七章将会探索联合社工和服务使用者的可能性。
然而,在焦点小组里,集体行动通常被认为是工人们联合的机会。关于新近的从业者论坛有很多讨论,这些论坛在21世纪社会工作检视(21st-Century Review of Social Work)的主持下,在苏格兰成立(Scottish Executive ,2006a)。尽管,大体上,社工对政府的日常工作持怀疑态度,认为政府自上而下,并离社工的日常关注很远。不过,“21世纪检视”这一过程本身得到了认可,它给社会工作者提供了额外的空间以分享优秀实践的不同面向。纵然,对于社工更好的方法他们自己去开创空间,通过非正式的工作会议或者工会,而不是参加外面组织的社工的会议。
21世纪社会工作检视苏格兰Valerie 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走了积极的几步:
“我们已经成功为社会工作者建立了一个社会工作论坛,我们每两个月会见一次面。在上一次会面时,我们正在寻找一些来自东欧国家、已经在这个X领域的社工朋友…通过走到一起,我们越来越惊讶有这么多的人数,还有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所以我们打算用这个论坛去思考一些提议,并把它待会给我们的管理者….考虑到我们的工作量,我认为我们很幸运能得到空间去做这件事。”
Frances 同样热衷于让社工们走在一起:
“这种组织类型对分享想法,分享创新的和有创意的实践很有帮助。”
对Murray来说,任何包含“将社工从与电脑的关系中抽离出来”的,像上面Valerie和Frances描述的社工从业者团体,都是积极的。他很清楚,这些小组不能被局限在个人队伍或地方政府,因为重点是“为社会工作正名而工作,用任何的机会去影响政策。”
似乎社会工作者做了很多事情来抵消管理主义的压力:
■ 相互提供支持;
■ 分享创新的实践方法以发展实务;
■ 保持个人对专业价值的承诺—几个焦点小组的成员出席了社会工作行动网络(SWAN)2006年利物浦和2007年在格拉斯哥的会议,主题为:“社会工作: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专业?”;
■ 关注与服务使用者和照顾者建立紧密的和有意义的关系;
■ 与被边缘化和受压迫的群体和个体一起,并为其倡导;
■ 为了社工、服务使用者和照顾者的利益尝试去影响政策。

几个隶属大团队的社工,有着很能帮忙的领导,跟一些他们觉得支持性的行动者小组建立了联系。一些人愿意发声,并关注高层管理,如有必要,愿意站出来说“不!”。然而,对大多数的焦点小组组成员来说,社会工作是一个相当的个人化的任务;人们根据他们特定的角色,在机构内部尽全力去支持服务使用者、照顾者、学生和同事以满足他们强烈认同的需求。
这就是说,焦点小组成员同时也是相关工会的成员,尽管他们认为社会工作的“去政治化”正在增加,对于他们个人来说,感到非常遗憾。
比如Murray,坚持认为要在工会中承担关键角色:
“在社工领域没有工会对我来说是危险的。”
Amy和Frances 将这种政治觉悟的缺失与当下社工学生所受到的教育以及社会广泛强调的个人责任的压力联系起来,同时,他谴责道:
“我已经提过,从大学出来后的人在理解更大的图景的差异。(?)”(Amy)
“我们现在在社会工作教育里的新标准不再明确讲反压迫实践。”(Frances)
Craig 在想年龄是否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在我最后一次罢工)唯一越过警戒线的是孩子和家庭(的社工)…还有社区看护…唯一站在警戒线上的是刑事司法人员和行政…当时我在想“这里发生了什么?”然后唯一能够想到的是那些社工还很年轻。”
Murray和Amy两人都有着超过35年的执业经验,然而,新进执业的Melanie,还很年轻,将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社会工作的去政治化直接联系了起来。举个例子:
“撒切尔主义和工作场所不能是政治的让我很震惊…我们周围所看到的都是政治的结果…那些政治家正在主导着社会环境。”(Murray)
尽管如此,焦点小组成员无法准确指出他们认为社会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走向堕落的。从结果上看,现代化已经完成了,他们承认道路是曲折的(they acknowledged the devious way in which modernization has been accomplished)。主流社会工作者清楚只有当他们寻找时间和空间去思考他们的工作生活,他们才能逐步开始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服务使用者身上的以及公共服务上的事情有完整的理解。不幸的是,这一章已经表明在主流机构里社工是没有多少珍贵的空间以这样的方式思考和反思的。然后,现代化进程实际上伤害了社工和服务使用者,而不是为他们改善他们所关心的事情,这是毫无疑问的。在社工了解它之前,那些曾经让他们深感忧虑的实践方法在社会工作的结构中已经建立起来了。
于是,直接听到主流社会工作者对受苦人们的关怀热情,是一个巨大的安慰,他们依然心怀承诺,保留着那些某种程度上满足服务使用者、照顾需要及权利的实践。在2004年,John Clarke 认为,尽管新自由主义议程的浪潮和公共领域不断受到打压,公共服务也继续存在,这确实,公共服务是抵御新自由主义最有害的因素的缓冲地带。
出于很多原因,公共领域(和它动员的附属物)是“砂砾”的一部分,阻止那想象的新自由主义世界体系顺场地运转。如果我们从寻找“砂砾”开始——关注顽强抵抗、抗争、干扰和未成功的规则——而不是在宏大的故事(big story)讲完后把这些砂砾当作收尾象征的一段丢进来,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会不一样。(Clarke,2004,pp44-5)
在本书参与主流社会工作焦点小组的社工不会将他们看作是极其顽抗的或者妨碍性的,但他们肯定是“砂砾”的一部分,他们以最适合自己方式进行抵抗,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已最适合服务使用者的方式进行抵抗。
编辑:李美霆socialworkweekly.cn








